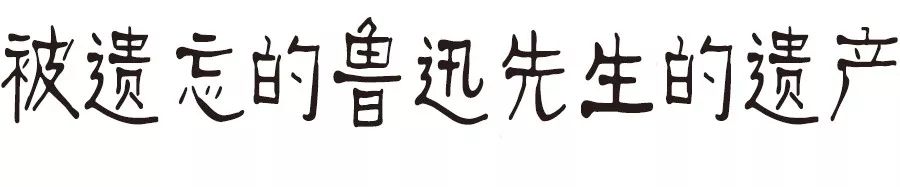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李浩 1971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20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孙犁文学奖、建安文学奖等。
文 / 李 浩 一 被遗忘的鲁迅先生的遗产——这个题目本身即属于“拿来”,它来自于米兰·昆德拉《被遗忘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被遗忘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还有另外一种翻译,董强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中译作“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我觉得对于鲁迅而言,他的某些遗产其实遭受着双重:“被遗忘”和“受到诋毁”。一方面我们忽略着他、遗忘着他,漠视他的努力和治愚的“痛心疾首”,将他的指出和警告抛于脑后,忽略他指出与警告的现实针对,而另一方面我们则借用另外的片面深刻、另外的似是而非、另外的价值确认来对鲁迅的某些珍贵遗产进行否认和诋毁。随着时间,“鲁迅”渐成为一个面孔、一个供于神龛上的纸片或一个代名词,他曾试图清理的泥沙在时间的河流中重又聚拢并且淹没他。 在《被遗忘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中,一向理性的米兰·昆德拉在文字最后把自己的语调升高,他以一副危险关头的卫道者模样伸出手来,郑重而带有庄严感地宣布:“我的回答既是荒谬的也是真诚的:我不以任何事物为归宿,我只皈依于已经被贬值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对于鲁迅先生的被遗忘与受到诋毁的遗产,我不得不时时自问,我是否有勇气谈及皈依,我是否敢于像米兰·昆德拉那样笃定?退一步,我和我们,是否意识到鲁迅先生的可贵遗产中有哪些是需要梳理和重新认知的,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二 小说,小说的。小说当然是鲁迅先生最为显赫的遗产之一,事实上鲁迅用他的小说写作为我们重新定义了“小说”这个词,它不再是“饰小说以干县令”,不再是轻质的、羽毛一样的事物,不再是简单的依靠传奇与怪诞的故事来取媚、来满足,而是将它赋以责任,赋以任务。启蒙,治愚,“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小说中充斥着启蒙精神,他指认问题,指认伤疤和痛苦之处,指认在我们的司空见惯里潜藏的麻木、愚蠢、荒谬、非理性、自私和吃人习性,指认我们的哀和不幸的背后深渊……鲁迅用他的小说写作为我们重新定义了“小说”这个词,它和启蒙与治愚紧紧联系于一起,它被赋予了以往不同的责任。在鲁迅之后,在五四那个时期之后,此时的小说绝非《庄子·外物》中“小说”的概念,它有了大,有了恢宏和对人的追问,有了对民族性的深切考察和贬斥,有了匕首和投枪的尖锐,有了反省与自省,更本质的,是它有了对于“用”的负重,尽管“用”这个词也并非旧有的概念所能言尽的。这个“用”,更多的是启蒙性,更多的是对我们认知的丰富和提升。 启蒙,治愚之用,是鲁迅小说中的可贵遗产,是鲁迅和他那一个时代的人为“小说”这个概念增加的新质,然而在一段时间以来它遭受着遗忘,甚至是诋毁。 在一段时间以来,“启蒙过时”“启蒙已死”“知识分子更应强化自我启蒙”,小说逐步又回到小上,它退向一隅,成为“无用之用”——很长一段时间我也认可无用之用,更多地强调趣味和审美,强调更为形而上的追问和智力博弈的快感,以及“非现实性”……但近年来,我在部分地修正自己的认知。我认为小说的启蒙性是小说存在的价值之一,甚至是首要的价值,它应当对我们的习焉不察提出警告,它应当让我们思忖我们的日常、习惯和潜意识的幽暗区域中都有什么,它应当让我们了解和理解那些不一样的他者,同时,我们也应更多地注意到“小说的心脏中令人不安的火苗”……启蒙,依然是小说家无可拒绝的责任,它甚至更为迫切。 说“启蒙已死”或“启蒙过时”貌似遵从着某种文学和知识的进化论,承认人类知识的叠加和前行,但它本质上是把启蒙性看作“阶段性”产物,言外之意是这个时段已经不是启蒙时段,启蒙时段和之后的他们也无法命名的时段有一个绝对鸿沟,完全无视启蒙的恒久性、持续性和渐进性,他们愿意谈及“每个时段有每个时段的任务和要求”,当然只有这样他们才似乎总是新的,总在提供新问题——无论这所谓的新问题是不是些新瓶里的旧酒,无论它是不是细枝末节的,或从政治家那里借来的旧物。说“知识分子更应强化自我启蒙”这话似乎没错儿,莎士比亚不会一贯正确,相对于上帝来说莎士比亚存在一千条错误,但这不是否认和漠视莎士比亚戏剧意义的条件,当然不是。问题是,我们在谈论“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时候,暗含的是否认知识分子的某些知识和智慧,因为它不符合我的主见不符合我以为的那些,不符合我所接受的教育;我们在谈论“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时候,其实也暗含了一个“知识分子最愚蠢”的轻漫,我们认为你的所谓启蒙其实更应当启蒙,你们其实远不如那些被启蒙者更聪明,因为你们不会做鞋子也不会建筑,不会修汽车也不会修自行车……说“启蒙已死”或“启蒙过时”,或多或少出于一种进步论的幻觉,似乎有了人工智能人人便都已人工智能,似乎经济的某种改善人的智识和人性会有一个同步的、整齐划一的提升和变化,似乎……但我们所见的事实是,在十几年、几十年的时代演进中有些东西是不能轻易演进的,而且时有退步,人对人和自我的认知依然滞后,人性中的某些固执恒定变化极慢,而被福楼拜称为“将会伴随人类整个历史的固有愚蠢”——先于理解之前做出判断的这种热情不但随着时代进程得到遏制,反而越来越显得固有而普遍……启蒙怎么会死?启蒙怎么会过时? 因为无视鲁迅的警告和指责,因为我们自以为可以排除于被启蒙之外而且启蒙已死,我和我们所见的,恰是鲁迅笔下那些人物的一一“复活”,而且变得更有活力和普遍性:这一点不需要什么举例说明,只要我们读过一点儿鲁迅,只要我们不是目盲,自然能够感到能够看到。义正辞严地谈论“知识分子更应强化自我启蒙”的那些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不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自我警醒而是阿Q的复活,他们暗暗地和知识分子划出了界线,悄然地移动了屁股的位置,更本质的,他们是想象自己掌握着判断知识是否正确、有效的唯一裁判权,掌握着“从人间到天堂之间那道大门的钥匙”。这种阿Q性的令人迷惑之处是,指责知识分子启蒙性、说他们更需要启蒙的往往是那些有高学历的人,拥有令人目眩的知识和能够说出大量引文的人,往往是那些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不是生活于未庄的不识几个字的农民…… 在一种合力之下,我们的小说一点点地祛除了启蒙的因质,我们似乎更强调文学的“无用之用”,无用之用上升为标准甚至是显要的标准,小说家们也乐得如此,他们更愿意小,更愿意细微,更愿意精致,更愿意退入某种艺术的安全地带,更愿意挖掘开表层的浮土揭示已经被之前的世界文学和中国作家已经“揭示”过一千遍一万遍的所谓“人性”……说实话,在这样的作品中我和我们看不到怎样新质的东西,只剩下一种简单重复,一种合谋的、局部的狂欢。 启蒙退却,进而是艺术退却,我们在宣布启蒙已死之后又匆匆宣布先锋已死、流派已死,那在小说中未死的还剩下什么? 我们,为什么这样愿意宣布死亡而不是展现发现新生的欣喜? 这,当然是个问题。 三 使我着迷的那些小说更多是因为书中所表现的聪明、智慧和道理,这正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即:变成以某种方式摧毁我心中批判能力的故事。这些故事迫使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了?”这正是我喜欢阅读的那类小说,也正是我愿意创作的小说。因此,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一切智慧的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在小说中出现,从根本上来说,都以某种方式要溶化到情节中去……在一则访谈中,巴尔加斯·略萨对采访他的记者理查多·阿·塞迪说道。“使我着迷的那些小说更多是因为书中所表现的聪明、智慧和道理。”——在鲁迅的小说中,使我和我们着迷的大约也恰是这些,是它所表现的聪明、智慧和道理,同时它对我和我们的习焉不察提出警告,让我们认识和审视我们的行为,我们民族性中的那些,我们所共有的软弱、怯懦、麻木和平庸的恶,唤起我们的羞愧,呼吁我们进行自我改进。 自我改进当然是艰难的,对孔乙己是,对阿Q是,对N先生是,对华老栓、赵老爷、陈世成同样是,没有人愿意吞下难咽的苦药,我们更愿意掩盖它,更愿意别人赞美我们甚至赞美我们并不存在的所谓美德。既然自我改进那么艰难,而且总会将自己的短和小显露给别人,于是我们就开始发明“视而不见”的方法,我们开始宣布能显示短和小、粗和劣的一切都已死亡,我们开始将一切能照见我们的短和小、粗和劣的镜子“义正辞严”地剔除,鲁迅先生的遗产已经属于可观摩但无实用的旧物…… 回到刚刚的问题,小说还剩下了什么?剩下了集体讲述倒霉蛋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将从小说开始的时候遭受一系列的悲剧和丧失,甚至不同人写下的不同小说里,主人公遭受的悲剧和丧失也大致相同,物质的不得和欲望的不得……他们貌似对所谓的底层有着同情但本质上只是对悲悯的消费,引得一些有三流社会学知识的批评家们趋之若鹜。小说还剩下人性,而这个人性被简化为欲望,是欲的得到与得不到,是得到了欲的怅然和“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的愤慨。在这一所谓的“人性开掘”之中我们更多见的是无事之非,它没有对星空的仰望,也没有对自我行为的步步逼问,它回避了属于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精神的甚至现实的向度,自我塌缩和矮化,是韩春燕指出的那种“室内剧”。那些掌握着简明读本的三流社会学知识的批评家们也对此趋之若鹜,只有那些能被他们所理解的知识才会让他们兴奋并有话要说。“开掘人性之谜”,就这点浅陋的欲望书写也能号称人性之谜,也能叫开掘或发现?这样的提供,比起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的提供是多了还是少了? 在莫言的、余华的、苏童的、孙甘露八十年代伊初的小说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共性问题,就是他们的小说中时常“权力在场而社会缺席、法律缺席”,这与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对公检法系统的破坏有关,而数十年后我们的写作中依然显得社会缺席、法律缺席,处在室内的人物不与社会和法律发生关系,而那些倒霉蛋也几乎不与社会和法律发生关系,生活只给他单一向度,他只是一个人在面对在承受……这种顺着前人的惯性一路写下来是不是一种堕性,是不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无能? 好吧,我们剩下的,就是讲述一个简单的、能让人不太费脑子思考的故事了,而这个故事,说实话多数人还讲不好,他们已经匮乏艺术的耐心,匮乏艺术的精心——当然耐心了精心了给谁看?掌握某些话语权、到处跑场子的批评家们试图在你的文字中寻找的不是艺术不是耐心,而是他理解的社会学知识…… 鲁迅的精心只属于鲁迅的时代。那些反复谈到“一棵是枣树,而另一棵还是枣树”的批评者们未必意识到它有什么好,他们谈及不过是出于人云亦云的惯性,出于对神龛上那张纸片不置疑的崇敬而已。在整个文化界,我觉得我们大约比任何一个可知的时代都浮躁、都麻木,它自然会体现于文字上和我们的小说中,体现于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中。我们是不是像布罗茨基说的那样,是一个二流时代的忠实臣子?不,我甚至觉得能进入所谓的二流都是极奢侈的事了,这,真是让人悲哀。“今天,现代性已经熔化在大众媒介巨大的活力之中,成为现代的意味着竭尽全力追随时尚,顺从,比所有最顺从的人都更彻底地顺从,现代性已经穿上了媚俗的衣服。”米兰·昆德拉在著名的耶路撒冷的致词中谈道。而顺从和退到安全区域的我们,遗忘了小说之用的我们,有意无意去除了启蒙性的我们,当然显得更为媚俗,甚至本身就是俗的核心部分。太多的人,太多的写作者,他们随世俯仰,在媚俗之流中如鱼得水,成为一种示范。他们不仅忽视和诋毁启蒙,而且还会轻视和诋毁标准、规则,以便在标准的阙如中获得更多。 强调文学的无用之用已经有十数年的时间,它成为了一种深入化的“流行”。强调文学对人性的挖掘也有十数年的时间,它们同样成为了一种深入化的“流行”。它,有它片面的合理性,但现在我们应当对它进行审视与更直接的追问了。 四 重新翻捡鲁迅小说中提到的那些名字:《阿Q正传》里的阿Q,《狂人日记》里的那个狂人,《祝福》里的祥林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所创造出的人物往往是弱个性、强共性的,他的名字是张三是李四关系不大,甚至名字的有无都关系不大,他往往会是一类人的人性、行为、精神内质和命运的“代言者”,具有更强的无中生有的性质,具有更强的寓言化的性质。他,产生于理念,就是在他的面部表情中也隐约可见“理念”的骸骨的移动。 我认为,强烈地认为,从理念中出发,选取我们民族性中的集体DNA加以萃取,让它们在经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后成为有着鲜明特质的“结晶体”,也属于鲁迅被遗忘的遗产之一,它原本值得重视。 在这里,鲁迅的人物当然源自生活。但绝非照搬生活中的已有,在他的小说中那些有名字的、没名字但被符号替代的个人都是他所创造出来的,为了帮助我们认知存在于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精神胜利法”,鲁迅无中生有地创造了阿Q这个人,他当然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中了民族性格的一类人,甚至是全体性的,它还以遗传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血液;“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寥寥也。(《鲁迅书信集·致许寿裳》)”——因由这一发现,加上“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再次无中生有,写下了《狂人日记》,创造出了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狂人。孔乙己也并非是一个个人,并非是鲁迅在当什么酒店学徒时的所见,而是创造出的,在这个孔乙己所集中的一类所谓知识分子的集体特征,他们至多是知道者,他们的所谓知识无法运用于生活,为生活和生命增添什么,然而却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伪、更多的僵化和自我辩解…… 在鲁迅那里,他是不屑于照搬生活的原貌和生活中的人的,即使那个人长了六指有特殊的跳跃能力,即使生活中的发生如何奇特如何让街坊乐道——小说的负重感让他不屑于如此提供,他愿意让自己的人物根植于理念,根植于对一类人的认识,是一类人甚至是这个民族共性的产物,而不是哪个具体的所谓独特。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写下的人物、写下的心理心态和民族性总能那么恒久地、持续地生活于“现实中”,是我们可见的身边人甚至是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写作是非现实的,他是在创造,一直在创造,他写下的每个人都与生活中的所谓现实中人不像,他并没有真实记录——把真实记录、把生活可以的发生看作是“现实主义”必遵的方法、必须的路径,其实是对小说的侮辱,也是对现实的侮辱,其实是无视小说创作的内在方法的一种粗暴而低劣的理论,是谬误和有害的,可是它竟然“成为常识”。作为作家、教师,在近几年的时间里我反复地谈论小说的虚构诉求,以“小说的魔法”为题或以“理念的烟和真实的‘魔鬼’”为题,谈论小说中的真实是种怎样的真实而即使最像现实的小说,其故事、其结构也是经历了种种设计的“魔法之物”,有些小说里的情节、细节,貌似生活生出来的,但它更可能的诞生地其实是认知和理念,只是作家的“仿生学”处理和逻辑能力让我们“信以为真”……然而在这一讨论结束之后,许多学生、写作者和批评家们还依然会回到他的旧有理念中,他们承认你讲述的正确,确是如此,但这绝不妨碍他们的坚固,虽然他们可能为找不到路径和不能出名而苦恼着。 他们信服鲁迅、敬仰鲁迅,然而信服的、敬仰的是“那个象征”,却完全不接受他所给予的那份遗产。他们选择性地接受知识,即使那个知识已经被证伪和反复地证伪。 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现实主义?张清华在《文学中的现实或真相》一文中谈道,“现实主义的话题,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难索解的难题之一。因为它很容易被认为与认知论的原则相联系——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因此,关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也伦理化甚至政治化了,乃至产生了现实主义等于唯物主义,等于政治正确的逻辑。这是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难以真正展开的原因。”是的,确实如此,出于某种理论上的先验正确,某些秉持僵化现实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根本没有进入文学内部、体验文学操作技巧的耐心和能力,也完全无视鲁迅在小说创作中的“创造性”经验以及这份经验的普适——你即使给他点出并深入解析了这一经验,他也承认这一经验的存在,但一到他和他的文学、他的文学观念,鲁迅的遗产就消失得荡然,那种选择性盲目让人感觉心寒。“当我发现以往的那种就事论事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述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余华的这段话在我来看是经验之谈,它和鲁迅在小说里呈现的那种“真实”是延脉的、继承性的,可是,为什么这一常识总是遭到漠视、忽略甚至诋毁呢? 五 “概念化”是我们诟病小说的习惯用词,作为小说家,我见多了同行们对这个词的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宁愿说自己完全是信马由缰,他们宁愿说自己根本不对小说过多考虑,有一个开头之后他的写作就像拧开了水龙头的水流——说久了他们也就信了,愿意听到这些的批评家、阅读者也信了,他们的写作也就开始信马由缰……近年来,中国小说普遍水准不高、价值不高、新意匮乏的原因,其实部分是由此而生,因为他放弃了对小说主旨性和人物设计主旨性的思考,信马由缰让他们不会具备理想和奔赴的野心,而这对于小说来说何等重要。 概念先行,鲁迅的诸多小说都有明显的概念先行性质,把“改变他们的精神”作为“第一要著”的鲁迅当然不会满足于描述日常生活中某些奇异的、新鲜的发生,他也不会满足于旧式文人岁月静好、顾盼自怜或感怀“怀才不遇”的狭小趣味——小说,在鲁迅那里是治愚的药剂,是启蒙,有着大负重。是故,被他所塑造出的“新人”多数不是直接源于生活的那类,他取的是DNA,是这个民族中共有的细胞核,将它们打碎、融解,重新组合,甚至是夸张地组合。“演变、着色和组合的各种效应在他们身上完成,从组合的元素里又生成新的中和物”,茨威格在《三大师》对巴尔扎克的写作说出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鲁迅,或者说更适用于鲁迅。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多是“新的中和物”,是经历过化学反应的奇妙的结晶体。在我们的习惯认知中,来源于生活、明显有生活印迹的往往会得到褒奖,而经过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由概念(理念)生发的则往往遭受诟病,“概念先行”似乎带有某种“原罪性”——这一经不起推敲的习见很值得商榷。取自于生活当然可以写出生动感人、气息浓郁的好小说,像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抵挡太平洋的大坝》,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何谓永恒》,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萧红的《呼兰河传》等等;而由理念生发、具有概念先行意味的卓越小说则更多,它更容易建立“精神高度”和“认知高度”。为了塑造、认知克尔凯郭尔提出的“那个个人”,知识分子只追寻真知和智慧而不依附、栖身于任何群体的独特孤独,意塔洛·卡尔维诺创作了《树上的男爵》,让柯西莫“一生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着大地,最后升入了天空”;为了追问人性之谜,为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寻找“依据”和展现,让·保罗·萨特创造了《禁闭》的戏剧,创造了《苍蝇》和《死无葬身之地》;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局外人》更明显地带有理念的性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沙之书》《小径交插的花园》,萨尔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这一类佳作同样不胜枚举。中国古典文学多有“概念先行”之处,许由、盗跖均是由理念需要而创造出的人物,庄子笔下的不知几千里也的鲲鹏也属于同样的创造。 这依然是常识,是鲁迅先生留给我们可供借鉴和学习的遗产。他毫不忌惮自己小说的人物来自“概念”,来自他对生活、民族性的认知,每个人物的出现与出场都是有承担性和负载性的,没有一个人是偶发的、随意的,没有一件事的发生是偶发的、随意的、脱离了主旨的,《狂人日记》如果不写下“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不是这一概念性的发现成为核心,鲁迅也许无意写下这篇小说,他在生活中见到再多的迫害狂也不能给予他真正的兴趣;我不知道我们的地图册上是否有未庄的存在,这个未庄里是否真有这样一位叫“阿Q”的先生——当然我倾向是无,或者说我确定是无——但鲁迅创造了它们,它们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恍然发现:在中国,未庄多着,在未庄,阿Q这样的人多着。 在谈及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篇解析文章中我说过,“概念先行”并不可怕,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恰恰相反,概念先行往往是写出好小说来的重要保证之一,它会让小说有骨骼感,会给予小说“魂魄”,会赋予小说统一和前行的趋动力。任何一部小说,如果写作者未曾至少有一个笼统的“想法”确立的话,它最终导致的可能是“统摄力”的阙如,小说是散掉的。在谈论小说结构的时候我们大约会重视小说的故事线,但每一篇小说(伟大的、优秀的、自恰的小说)都有一个暗含的主题线,它应当“事先”在构思的时候确立下来并始终影响着故事方向。 这是小说的内部技艺,是鲁迅的写作告知我们的,属于他的遗产之一。 六 “总之,我们要拿来”——“拿来主义”在我看来是鲁迅先生最伟大的遗产之一,他要求我们凡是好的、优的、可用的都可拿来,而有些低的、劣的、错的、谬的则可或存放或毁灭,而不是简单地封闭住自己,让自己不闻不看不见不拾,甚至将所有外来都视为洪水猛兽。 因为恐惧而不敢拿来,因为未见识而不知拿来,因为经历过洋枪洋炮的打开而敌视拿来,或者,更因自己那种先于理解之前的判断而将一切洋的、外的、非本有的都其心必异的“阴谋”,自然属于不智。在文化中,还有一种对“拿来”的拒绝,那是一种对于吃了羊肉会长成羊的恐惧——事实上,无数的具体例证早已证明吃过羊肉、牛肉或三文鱼的肉只会生长你的肉,没有一个人具有吃过羊肉就长成羊、吃过牛肉就长成牛的特异功能,它只会出现于像古希腊的《变形记》或古中国的《山海经》一类传说中,是想象和幻觉的产物。没有人如此长成过但不妨碍我们时常担心,而这种担心又是那样的坚固。 对拿来的拒绝:还有一种理由是,“拿来”属于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它会造成你的无根,它会让你丧失泥土而成为漂泊之物——印度的泰戈尔接受着英国的文化甚至使用英语写作,他也没有失掉自我的根、文化的根,我们不会把《吉檀迦利》读成一本英国的书;卡夫卡那样敬重老子、庄子,也依然是德语作家,他并没有漂至中国成为中国作家;徐悲鸿在法国学习了油画,他归国后画下的中国事物也依然属于中国,好吧,就是讲述中国故事、非常中国化、主流化的《红色娘子军》,它可是一部芭蕾舞剧,这一剧种完全是西方的;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其交响乐版也颇受好评——交响乐也并非我们旧有文化中所有。即使在那个时代中,我们的文学艺术也没有中止拿来,外来方法、乐器和技术的运用同样能作用于服务于这片土壤。无论怎样的技艺方式,无论怎样的风格结构,如果你用它来说你的内心,说你的所见、所想、所感,它就是你的,就会成为你的一部分,极为有机和有效的部分。 “拿来”是种主动和自愿,是我要接受,主体在我,我接受的事物可能莫问东西,在这里的“我”就是克尔凯郭尔的那个个人,在这里哪有什么文化侵略?我看到的不过是你试图将你以为的标准化物件塞进我的头脑中的强势;至于泥土和根,主体依然是我,是我要在我的写作中画下属于“我的个人的缪斯的独特面部表情”,最终,我都会在吸纳的过程中逐步摆脱来自于外来的、中国的、同乡写作者的影响焦虑——我总不能让我的写作长得不像莎士比亚,而像曹雪芹就行啦?抄一遍《三国》会比抄一遍《奥德赛》更让人敬重? 还有一点,你能举出几部所谓有根的本土化的小说,它明显未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并且是得到这个时代的聪明人普遍服气的么? 我们的现代小说从本质上说不是本土的产物,我们更多的是拿来的,从欧洲,从当时的苏联。“现实主义”这个词也不是源于本土的,据说现实和主义这两个词就都来自日本。我们已经少见志怪和传奇,也没见多少作家一生使用笔记体、章回体写作而且获得批评家们的重视,可这不妨碍他们树立荒谬的地域标准,坚持着对拿来的拒绝。 一种思维、一种思潮或一个概念,无论它的里面包含着多少莲花,多么美妙或多么义正辞严,只要你能够寻到一个反证它就只会是局部真理,如果你能找到五个或更多的反证,那它就值得警惕,其实你已经部分地证伪了它……但有时,甚至更多的时候,常识时常无力。 前段时间读到残雪的一篇文字,微信的题目是“中国作家的自卑情结”。她谈道,“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们大开眼界,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使文学得到了空前发展。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步步地退化,再也没有向前发展了。我认为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积弱已久,当时的那种摄取也是浅层次的,我们的文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气魄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营养了。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作家写过两三部东西之后就空掉了,江郎才尽,转行、用劣质品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是因为绝大多数一开始就没有诚心诚意地去向人家学,只想从人家那里捞点技术过来就算了,只有自己家里的东西使起来才有把握。可说是心里发虚,投机取巧。学习西方经典是一件要命的事,每天要解剖自己,谁受得了啊? ”当然是一家之言,但这一家之言中有极为有益的片面深刻,我同样认为我们拿来得不够,至少就我自己而言如此。 鲁迅,大约也会觉得我们拿来得不够,还远远不够。当他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诸多的作家、学者和阅读者一片叫好的时候,鲁迅先生毫不避讳,他坦诚自己的写作有所拿来,并告诉我们,你们感觉我的这篇小说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的横空出世,其实是你们阅读国外的小说太少了,他们的好作品可多着呢,在我写这个《狂人日记》之初,事先就读过果戈里的同题小说……而在鲁迅先生晚年,他几乎完全地停止了自己的小说写作而将精力用在对域外小说的翻译上,而这一翻译工作一直延续到他的临终之前。为何如此?是鲁迅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是翻译家,还是他已经江郎才尽,不得不依靠翻译来养家了? 不是,当然不是。鲁迅的本意应当是想将国外的、那些有益的(至少是他认为有益的)文化、艺术“拿来”中国,让它们裨益我们民族,裨益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让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有效的并且更为卓越的提升……是鲁迅先生,把这项任务看得更为迫切。 “拿来”,别求新声于异邦,催生自立自强、科学理性、平等博爱的新国民,是鲁迅贯穿了整个文学生涯的内在诉求。据不完全统计,鲁迅的文学生涯由翻译始并由翻译终,他一共翻译过近两百位作家作品,达三百万字之多……“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鲁迅的这段话,我自觉它有某种的振聋发聩,然而这一遗产,却也在被遗忘的过程之中。 青年作家 YoungWriters 新青年 新文学 新经典 >>>>>>访谈<<<<<< 第01期 |
- 关注天气: